
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,在党的坚强领导下,新中国的文化生产力充分释放,城市的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,文艺界创作繁荣、评论兴旺,稳步进入了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新时代、好时代。为了多门类、多角度、多层次地回顾新中国文化工作、文艺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,为打造文化自信自强上海样本、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踊跃建言,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与本微信平台联合举办“扎根人民,与时代同行—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·文艺的春天”文艺短评笔会。
文艺家、评论家踊跃来稿,以75年来印象最深刻的文艺作品、文化活动、文化事件等为题,回忆接触作品之过程,抒写审美体验之感受,品评文化价值之所在,瞻望文化发展之前景,表达“更紧密地团结,更勇敢地创造,文艺工作者永远在路上”的主题。
问鼎诺贝尔文学奖有几多重
新利18体育陈勤建

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,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,我国文学创作如怒放的春花,一片繁华,全国著名的文学刊物,发行量动辄数十万,直至上百万,包括当时民协的小小的《采风报》,发行量一度冲到了183万份。面对这辉煌的文学硕果,一批文学创作者,特别是一些著名的作家陶醉了,开始寻问,中国文学如何走向国际?何时能拿诺贝尔文学奖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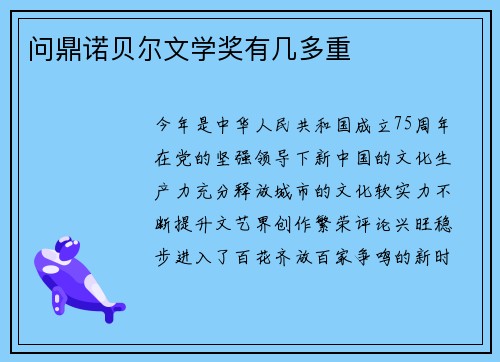
于是,经过精心策划,在一位国内作家大咖率领下,一群国内的著名作家,邀请了几位国际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和一批国际媒体记者,集聚在上海金山石化基地新建的,当时的上海第二个涉外住宿机构上海金山宾馆,闭门交流。国内闻讯赶来采访的一百数十名记者,全被挡在门外。
我国的文艺要走向世界,障碍在哪里呢?国内的作家、艺术家、批评家们的认识似乎是比较模糊的。有人怪罪于我们的作品没有很好的译文,有人认为这是因政治、社会制度不同导致的歧视,有人以中国的关系学审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,叹息没有敬礼铺路,招徕青睐。实际究竟如何?
同是时为社会主义国家,苏联肖洛霍夫以史诗般的《静静的顿河》名列诺贝尔文学奖的金榜;同为第三世界,危地马拉阿斯图里亚斯、哥伦比亚加西亚·马尔克斯等也分别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。由中文衍化出去的日文要说翻译难度似乎比中文好不了多少,可是,川端康成的作品,没听说有什么文字不懂的纠葛,也登上了同样的宝座。有人可能要说,川端康成的政治思想倾向与我们相背,故能得宠,那肖洛霍夫呢?何况,川端康成1968年以他的《雪国》《古都》《千只鹤》为代表,获诺贝尔文学奖。诺贝尔文学奖,作为文学走向世界的一种标记,贴标时难免不杂外界人为的因素,光凭粥少僧多就使它难持公允。然而,它毕竟不是滥发资金、乱贴标记、哗众取宠的。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以来,确实授给了一批世界公认的伟大作家。泰戈尔、罗曼·罗兰、萧伯纳、托马斯·曼、艾略特、海明威、川端康成、肖洛霍夫、阿斯图里亚斯、辛格·加里亚、马尔克斯、戈尔丁等。他们的获奖作品风骨峭峻,千姿百态。但有一点却是异曲同工,即在自己的作品中深刻而形象地展示了社会人生固有的传统。兼有文艺批评卓见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略特,在他的文论名作《传统与个人才能》中,强调一国的传统在作家优秀创作中的重要作用,“不仅其最优秀的部分,而且最独特的部分”都是它影响的结果。
著名作家冯骥才,会议中途出国访问,回来后对上海《文学报》记者说:“访加归来,我更深地领悟到,只有具备鲜亮的民族特色,才能走向世界。西方和我们观念迥异,东方人好求同存异,而西方人却掩盖相同的,摊出不同的。西方人不喜欢自己和你一样,也不希望你们和他一样。我们模仿西方,似乎能迎合,然异邦反不接受。有出息的中国作家应当有与西方拔离的意识。”后来,中国有了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。
(作者系上海市非遗保护工作专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、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、上海民协原副主席)
美编 | Yep
未经许可,禁止转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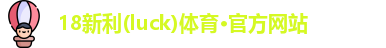
发表评论